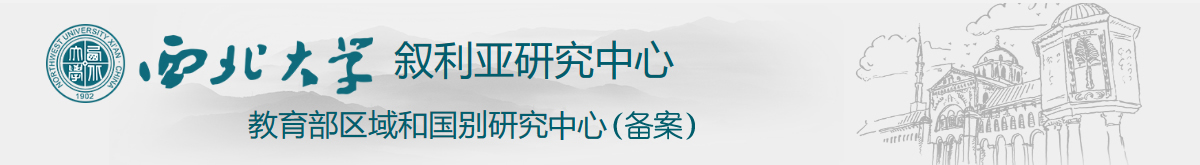叙利亚内战爆发七周年之际,西北大学叙利亚研究中心公众号将分享和回顾中心主任王新刚教授关于叙利亚问题的系列论文。今天分享的是王新刚教授发表于《西亚非洲》2015年第5期的文章《哈菲兹·阿萨德时期叙利亚政治体制解析》。
哈菲兹·阿萨德时期叙利亚政治体制解析
王新刚 马帅
内容提要 哈菲兹·阿萨德在1970至2000年长达30年的统治期间,依靠血缘、部族及亲信的忠诚以及个人魅力,在叙利亚建立起一党制总统威权政治体制,通过军事安全部门、复兴党和官僚机构三大支柱,实现了其对政权的高度垄断。阿萨德当政时期,叙利亚政治体制具有明显的新威权主义、少数派统治、世俗化政权等特征,这是该国特定的政治进程中的产物。然而,阿萨德建立的体制未能解决独立以来民族国家构建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即如何在一个高度分裂型和冲突型的社会中实现权力的相对平等与有效分配。2000年,巴沙尔虽然继承了其父的政治体制,但是这种体制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如故。
关 键 词 政治体制 叙利亚 哈菲兹·阿萨德 威权主义 复兴党
作者简介 王新刚,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710069);马帅,西北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生(西安710069)。
2011年3月以来,叙利亚爆发严重的政治动荡与危机,并演变为内战,持续至今。叙利亚严重的社会分裂、教派冲突、经济困顿及不平等固然是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但从历史的维度看,叙利亚危机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叙利亚复兴党制度构建和国家治理失败的结果。20世纪70年代,哈菲兹·阿萨德凭借卓越的领导才能,在阿拉维派、叙利亚复兴党(以下简称“复兴党”)及其军队的支持下,构建起一套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叙利亚由此摆脱了自20世纪40年代独立以来政局动荡、政变频仍的局面,使叙利亚在中东地区复杂的矛盾漩涡中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地区强国。然而,阿萨德构建的政治体制并没有真正解决叙利亚存在的复杂而深刻的社会、经济和宗教及教派等矛盾,反而加深了社会的隔阂。本文希望通过对阿萨德时期政治制度的研究,挖掘叙利亚乱局的根源,并有助于预判叙利亚危机的未来走向。
阿萨德时期政治体制产生的背景
阿萨德时期政治体制的建立,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叙利亚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需求,即要求建立强大的国家、摆脱政治动荡、促进经济发展,这是因为“现代化的进程客观上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力量核心——权威政治的有效统治,以便形成一种稳定、秩序和发展的环境。”[①]另一方面,它也是阿萨德作为权力欲极强的现实政治家运用政治手腕与个人魅力达成自身政治目标的主观结果,“除了对权力的强烈追求,他还感到自己肩负着对国家和人民的一项至关重要的使命,即叙利亚在他的领导下得到统一并发展成为区域强国。”[②]
(一)阿萨德体制建立前的叙利亚政治生态变迁
叙利亚现代政治发展肇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奥斯曼帝国崩溃之后。此后,现代叙利亚政治经历了委任统治、议会民主和复兴党一党执政等三大历史时期。[③]从现代化理论视角来看,叙利亚在构建民族国家以及实现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选择何种路径以及依靠何种力量来推进现代化的问题。
1946年,叙利亚摆脱法国委任统治获得独立,但国家却深陷派系斗争和军人干政的泥潭而举步维艰。独立之初,国家政治体制延续了法国委任统治时期的议会民主制,这一政体脱胎于1930年宪法基础上的宪政体制,带有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是西方强行嫁接的结果,与战后的叙利亚经济基础、社会结构与价值观念格格不入。由于独立初期叙利亚处于“马赛克式”的政治生态,政治斗争中夹杂着个人、家族、教派、主从及地域间的利益矛盾和认同关系,因此,议会民主制造的就是一个孱弱不堪、内阁频繁更迭的政府。这样的政府不仅无力应对国内现代化发展的要求,而且面对错综复杂的周边地缘环境和大国政治斗争时也是力不从心。内外交困严重削弱了政府和体制的合法性,政治生态实际上陷于权威缺失的衰朽状态。1949年,叙利亚军人集团连续3次发动政变,标志着议会民主政治开始走向崩溃,同时也开启了军人干政的“普力夺社会”“普力夺社会”是指政治制度化程度低的社会。亨廷顿指出,在这种社会里,它不仅指军人干政,而且指各种社会势力都干政。[④]叙利亚政治进程步入急剧动荡的历史时期。
1958年,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复兴党的推动下,叙利亚与埃及合并建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但由于埃及的政治清洗以及纳赛尔的专断独裁,叙利亚不久就脱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尽管复兴党在阿联期间经受了严重挫折,但通过建立军事委员会与军队合作等方式,复兴党很快又在政治斗争中占据优势,成为叙利亚政治生活的主导力量。正如亨廷顿所言,“欲根除国内政治的动荡和衰朽,这些国家必须树立起强大的政府,舍此无他路可走;强大政府的构建和维持仅仅依赖强大政党的缔造和巩固,而政党的强大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力量。”[⑤]复兴党作为超越穆斯林和基督徒不同教派的、具有不同社会背景的、体现超越传统家族势力、地区利益和教派分歧之狭隘界限的民众性政党,特别是作为意识形态鲜明、政党目标明确和组织机构健全的政党,有着较强的政治动员能力。“1963年的‘三·八’革命和复兴党政权的建立是叙利亚政治发展过程中重要的分水岭”,[⑥]它彻底改变了叙利亚的政治进程。1963年政变后,叙利亚初步建立起一党执政、党政合一的政治体制。
然而,叙利亚复兴党的发展壮大,也孕育着自身的分裂和冲突。1966年“二·二三”政变后复兴党激进派彻底将元老派排挤出党,并推行更加激进的严重损害城市工商业阶层利益的所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加之“六·五”战争惨败对复兴党政权威信造成的沉重打击,使复兴党领导层再次面临分裂。1970年11月,身居国防部长要职的阿萨德发动“纠正运动”上台执政,在推行一系列政治、经济等改革之后,他凭借一党制总统威权政治体制实现了国家稳定。
(二)阿萨德个人政治抱负与主观努力
阿萨德之所以能够登上权力顶峰,不仅因为他一贯狂热地追求权力,也因为他具备非凡的个人魅力及政治智慧。
1930年10月6日,阿萨德出生于叙利亚拉塔基亚省卡尔达哈的一个农民家庭,属穆斯林什叶派中的阿拉维派。[⑦]这个教派自公元10世纪形成后一直被认为是异教徒,世代遭受逊尼派的歧视和凌辱,但也使他们养成了逆境求生的坚毅性格。阿萨德深受开明的父亲影响,[⑧]自青少年起便胸怀大志。他14岁离开家乡,进入一所中学读书,在入学注册时将自己的姓名改为哈菲兹·阿萨德。“阿萨德”在阿拉伯语中为“狮子”之意,代表着尊严与力量,“哈菲兹”意为“保护者”。阿萨德16岁时加入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成为该党最早的党员之一,负责在学生中秘密建立基层组织。他以青年人特有的狂热,积极宣传复兴党政治主张,并担任学生运动的领袖。1952年,22岁的阿萨德弃医从戎,考入霍姆斯军事学院,后又转入阿勒颇空军学院学习飞行。1955年初,他因出色的飞行才能毕业时获得最佳飞行纪念章。此后,阿萨德屡获战功,晋升飞行中队队长,并被派往苏联学习夜航作战技术。但阿萨德无意追求单纯的职业军人生涯,他只是把服兵役看成是应尽的义务和参与政治的手段。当时的叙利亚政坛政治斗争复杂,政权更迭频繁,阿萨德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以叙利亚复兴党军事委员会成员的身份多次参与政变。1963年,复兴党政变成功后,作为重要领导成员的阿萨德开始进入权力高层,出任空军司令。1966年,复兴党内部斗争加剧,阿萨德在复兴党地区委员会副书记贾迪德发动的政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政变后出任国防部长兼空军司令,与贾迪德一同成为复兴党两巨头。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失败,导致党内“责任之争”异常激烈。以贾迪德为首的地区委员会内外政策也日益激进。1970年11月,务实派阿萨德以“纠正运动”为名拘捕囚禁贾迪德等人,夺取国家最高权力。
从阿萨德的个人阅历与从政经历可以看出,阿拉维派的出身塑造了阿萨德坚毅果敢的性格,阿拉伯复兴主义赋予他人生志向与政治追求,漫长的军旅生涯与激烈的政治斗争使阿萨德积累了丰厚的政治资本和政治智慧。“在他眼里,只要目的正当,就可以不择手段。”[⑨]阿萨德依靠他在军队奠定的地位与势力,凭借自身杰出的领导才干,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化解了一次次危机与挑战,在军队中和政坛上迅速崛起,最终登上权力顶峰。
阿萨德时期政治体制的结构
阿萨德时期叙利亚政治体制的最大特点是总统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阿萨德依靠家族与亲信集团建立起个人权力中枢,牢牢掌控国家最高权力。政权的中坚力量则是军事安全机构、复兴党组织机构以及行政官僚机构。三大支柱分别在国家安全、意识形态和行政管理与社会整合方面发挥各自的作用,成为阿萨德政权强化政府能力、维持政治稳定的重要工具。人民议会、全国进步阵线及社会团体和群众组织则作为阿萨德权力结构的辅助机制满足政权对社会成员的渗透、整合和控制。以上3个层次相互协调,彼此联系,共同筑起阿萨德政治体制的权力结构。
(一)总统集团
阿萨德上台后,在叙利亚推行总统制,并于1971年当选为叙利亚总统。1973年,叙利亚新宪法颁布后,进一步确认了叙利亚的“总统共和制”政体。从1971年当选总统到2000年去世,阿萨德是历次叙利亚总统选举的唯一候选人和当选者。总统作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集大权于一身。然而,现实的政治运作不可能由一己之力来完成,在阿萨德的周围还有一个由家族势力及亲信下属组成的小集团,它与总统共同形成一个权力中心,凌驾于军队、复兴党和行政机关之上,并利用它们进行统治。
第一,总统权力独大。“叙利亚宪法赋予国家总统的权力,反映出总统的职权范围是远远超越国家其他机构的特点。金字塔式总统制的权力结构导致法定权力和事实权力都集中在国家总统一人之手。”[⑩]1973年叙利亚宪法赋予总统行政、军事、立法、外交等方面的绝对权力。“总统代表人民行使行政最高权力,会同内阁磋商制定国家的总政策,任命副总统、总理、副总理、部长和副部长,接受内阁成员的辞呈并解除内阁成员的职务;总统为军队和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可以发布一切必要的决定和命令;总统拥有解散议会的权力,在议会闭会以及出于保卫国家利益与安全的紧急情况下,总统行使立法权;总统有权宣布和终止紧急状态;总统有权宣布战争、总动员和媾和”。[11]我们从这些宪法条文可以看出,国家的立法权和决策权实质上都由总统及其幕僚一手掌控,议会只不过是一个象征性的表决机构,而所谓司法独立也同样是一纸空文。除了宪法赋予总统的广泛职权外,阿萨德作为复兴党领袖还兼任党的民族委员会及地区委员会的总书记,并且担任政治协商组织——全国进步阵线的主席。这样,凭借宪法条文的保障以及现实的政治运作,阿萨德实际上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且凌驾三者之上,牢牢地占据着权力的顶端。[12]
第二,以家族势力为核心。阿萨德时期叙利亚情报机构与安全部门大部分由与阿萨德同一教派的阿拉维人组成,并全部由来自阿萨德所属的马塔维拉部落家族成员指挥;突击队和禁卫军则由阿萨德的近亲指挥,士兵也大多是与其同乡的阿拉维人。阿萨德的家庭成员更是占据着政府部门的关键职位,其两位胞弟“里法特是规模庞大的禁卫军司令,贾米勒是穆尔塔达民兵司令,负责保卫拉塔基亚地区的阿拉维社团”;[13]“内弟阿德南·马赫卢夫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仍在政权中占据重要地位,指挥着拥有2 000人的共和国卫队,负责保护总统官邸”;[14]堂弟阿德南·阿萨德主管特战队,负责大马士革地区的安全保卫。其他两位家庭成员尤苏夫·阿萨德和穆哈默德·阿萨德则分别掌管哈马地区的复兴党机构和驻扎在阿勒颇的特防卫队,这两个地区是阿萨德政权的穆斯林反对派主要活动区;阿萨德的亲戚加齐·坎安是叙利亚军队驻黎巴嫩情报机构的首脑。阿萨德次子巴沙尔·阿萨德子承父业接管政权,至今依然是叙利亚总统,而巴沙尔的弟弟迈哈尔·阿萨德则是仅次于总统的二号人物,如今是叙利亚军方的最高掌权者,掌控著名的第四装甲旅、总统卫队和共和国卫队,同时是叙利亚情报部门的实际掌门人。
第三,培植亲信集团。阿萨德统治时期,将国家权力运行机制创造性地分为“一明一暗”两个系统。一个是基于叙利亚宪法与复兴党党纲的官方权力体系,包括议会、各级政府及复兴党组织机构,这个形式上的权力体系负责国家日常事务及社会运行与控制。在这层“合法性外衣”里面,存在着一个以阿萨德为首的非官方权力机构,它控制着国家的各个权力中心。这一实际操控机构的核心是阿萨德亲信集团形成的一个小圈子,或称“贾马阿”。“贾马阿”,阿拉伯语意为“集团”。[15]“贾马阿”由十余个在情报系统、安全机构及精锐部队中担任要职的人员组成,又被戏称为“十巨头”。这个小圈子忠诚团结,他们中的多数人均为与阿萨德关系密切或共事多年的老同志,对阿萨德言听计从,贯彻执行阿萨德的所有重要决策。在“贾马阿”中虽然有少数忠于阿萨德的逊尼派官员担任内阁和军队的高级职务,然而,在事关国家安全与政权稳定的要害部门中,“安全和情报网络机构、特种部队(2万人)和共和国卫队(2万人)几乎全部由阿拉维派人主管,这是阿萨德执政的坚强基石和安全保证。”[16]阿萨德的这种做法虽然有助于提防占人口多数的逊尼派的反叛,可以有效保护自身的安全,但机会的不平等招致逊尼派穆斯林及普通民众的不满,成为政治不稳定的潜在隐患。
(二)三大支柱
阿萨德为确保一党制总统威权体制的政治秩序,构筑起庞大且忠诚于政权的军事安全机构、复兴党组织机构及其行政官僚机构,并将其转变为阿萨德治下的三大权力支柱。
第一是军事安全机构。多年来,叙利亚军队一直是政治权力的基础,并不断干预政治,能够获得军队的支持对任何一位当政者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17]军人出身的阿萨德深知军队在政治斗争和维护政权中的重要作用,始终把军队作为巩固政权的重要手段。军事安全机构是阿萨德体制最忠诚且最主要的捍卫者,它主要由军队、警察与宪兵系统、安全及情报部门等构成。该机构规模庞大且自成体系,担负着维护国家安全、镇压反政府力量及巩固阿萨德个人权力的重任,是叙利亚国家与阿萨德政权的重要支柱。阿萨德时代,叙利亚军事安全部门人员待遇十分优厚,大量来自社会各阶层的青年争相加入,其规模也迅速膨胀。同时,这些青年在被纳入国家体制后,转变为中产阶级,从而扩大了阿萨德政权的社会基础。“至20世纪90年代,全国武装力量总人数达43万之多,再加上警察和情报系统10余万人,以及附属于军队的公司、企业、研究机构雇佣的文职人员,整个安全体系雇用了近一半的国家公职人员,占总劳动力人口的15%左右。”[18]这样,大量的人才通过军事安全机构被整合进庞大的国家机器中,它不仅有利于统治集团本身遴选人才,也便于国家控制社会。同时,军人的纪律和尊严感也易于激发群众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从而有助于增强国家的凝聚力,维护政权的合法性。
第二是复兴党组织机构。1973年,叙利亚宪法第八条规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是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党。[19]复兴党拥有为数众多的党员以及群众基础,党的纲领就是国家的主导思想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党的组织机构发挥着凝聚精英、调控权力、整合社会的重要作用。政府、军队的要害部门均由复兴党要员领导,主要的社会团体如工会、商会、妇联、各类行业联合会及高等院校的负责人也均由复兴党成员出任。入党成为民众进入权力体系的唯一通道,所有精英的选拔,任何人才的招募,均通过党组织进行。“自20世纪70年代起,复兴党规模不断壮大,其成员总数1974年为16.3万名,1984年扩增到53.7万人,1992年则达100万人。”[20]复兴党庞大的规模以及雄厚的社会基础为其进行政治动员与社会整合提供了条件。复兴党在叙利亚各地和各部门都设有基层组织,其组织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复兴党的党部监督各级政府,参与中央、地方的政治与经济决策,并向复兴党的中央机构——“地区委员会”负责。此外,复兴党还通过直接控制军方和警察局等部门,设立情报机构和国家安全机构,以便对叙利亚政府、军队以及各类社会团体和教育机构进行监控。
第三是行政官僚机构。叙利亚的权力集中于总统,叙利亚官僚机构没有实权。但后者的作用、地位亦不容忽视。除行使具体的行政、社会管理职能外,官僚机构的作用还体现在社会控制与整合方面。“只有高效率的机构,而不是个别的无限忠诚的军官们,才能保证有效地控制奖赏、惩罚和象征符号的持久力。只有国家机构能使对国家的社会控制不断发生变化。”[21]伴随着政府官僚机构的膨胀,文官的规模不断扩大。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公职人员人数已达70余万,约占劳动力总人口的20%,而其中60%可称之为官僚阶层,其增长速度是同期人口和劳力增长速度的两倍多。[22]由此形成的庞大的官僚阶层,客观上起到了吸纳和控制中产阶级、维护政治稳定的作用。同时,与官僚阶层相伴的是基于血缘、地缘和职业的裙带关系网络,国家对社会整合、控制的范围也因此进一步扩大。由此,国家的统治便延伸至社会的最基层,进而发挥了社会的控制、整合作用。
(三)辅助机制
国家的强大集中体现为,“国家有能力使民众服从它的要求,参与它领导和控制下的体制,并认可体制的合法性。”[23]阿萨德当政时期,人民议会、全国进步阵线以及各种社会团体和群众组织是阿萨德作为政变上台的领导人在政治民主化方面做出的改革努力的结果,虽然这些组织不可避免地处于威权体制的阴影之下,但正是这些组织的存在使阿萨德政权有别于之前的军人独裁统治,并且扩大了政权的基础,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现代化进程中民众政治参与的诉求。
第一是人民议会。1971年2月21日,叙利亚人民议会成立,此届议会的议员由复兴党临时委员会任命。1973年,宪法确认人民议会是国家立法机关,每四年举行一次选举。其职能包括:提名总统人选、通过法律、讨论内阁政策、接受和批准议员辞呈、撤销对内阁成员的信任、通过国家预算与发展计划、批准有关国家安全的国际条约和协定等。[24]实际上,人民议会自建立以来就只是一个咨询机构,处于政治决策的边缘,没有真正的立法权,仅有一定程度上的监督权。“对于政权,议会的主要职能是代表不同的地方和集团利益,而不是成为一个独立的决策机构。”[25]尽管如此,议会在维护阿萨德政权合法性、扩大政治参与方面发挥的政治功能难以替代。首先,人民议会是政权合法性的一种标志。尽管议会权力弱小,甚至形同虚设,但它毕竟是当权者所宣扬的民主共和政体在形式上的象征,因此具有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宣传功能。而且,议会通过法律机制和正规程序进行活动,其本身也说明政权具有一定程度的法理性基础。其次,人民议会起到了社会控制和政治诉求的表达功能。尽管议会并不能代表所有公民的利益,对那些作为政权社会基础的群体和组织来说,它仍不失为一种重要的政治或利益诉求渠道。因为议员来自军队、工会、农会、妇联以及各种职业群体,不管他们是由选举还是任命产生,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地区基层和利益集团的利益,反映了他们的要求和呼声。议员们纵然不能直接影响国家的政策,但他们的利益表达会潜移默化和间接地影响上层集团的决策。而统治集团也能通过这种途径体察民情、了解民意,从而有利于政权的统治。事实上,随着社会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社会利益的日趋复杂化和多元化,人民议会所起到的利益表达功能也进一步扩大了。
第二是全国进步阵线。1972年,叙利亚成立了具有统战性质的政治协商机构——全国进步阵线。它是联系和拉拢叙利亚各派政治力量的平台。[26]该机构承认复兴党的领导地位,“共和国总统及复兴党总书记是进步阵线的主席。”加入进步阵线的叙利亚党派主要包括:民主社会主义联盟、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社会主义统一运动、叙利亚共产党、阿拉伯社会党等。全国进步阵线名义上是为了增强进步力量之间最大限度的团结,以共同对抗犹太复国主义的侵略,但实际上旨在笼络和控制叙利亚其他政治力量,扩大统治基础,同时孤立反对复兴党的派别。在复兴党的压力下,它们同意复兴党占据多数席位,并接受其领导,将其政策和决议作为整个阵线的基本路线和纲领,同时限制它们自己在军队、学校以及其他社会群体中的政治活动。作为回报,复兴党将内阁、议会以及各级国家机构中的一些次要职位给予它们,并允许它们有最低程度的政治自由。通过这种手段,阿萨德政权将这些政治力量整合进了政权体系。这不仅笼络、削弱了这些政党,并将它们的群众基础加以改造,转变为自己的社会基础,或至少将它们所代表的社会利益群体控制在政权有效的统治范围之内;而且,孤立并分化了复兴党潜在的政治反对力量,促使它们之中的温和派效仿同一阵线中的政党,进入政权体系之内。阿萨德曾这样论述:“我们之所以强大的原因在于内部的一致和国家的团结,在于统一的全国进步阵线和英勇的武装部队。”[27]作为政治协商机构,全国进步阵线的作用表现在;团结各方爱国进步力量,扩大复兴党的民众基础,稳定国内政局等方面。各党派通过进步阵线实现了参政议政的目的,消除了多年来党派战争的局面,叙利亚国家政治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28]
第三是社会团体与群众组织。在阿萨德政权治下,各社会团体的政治参与是在政府控制下实现的。当时,叙利亚社会团体和群众组织数量众多,均在执政党控制之下,成为半官方或半政府机构。这些组织和工会有:工人总联合会、全国妇女联合会、革命青年联合会、复兴党童子军、叙利亚学生全国联合会、农民总联合会以及各种职业联合会,[29]“除了工会,这些组织没有任何社会基础,它们的设立是为了确保政权从上到下对社会的控制。”[30]它们实际上代表了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在阿萨德体制下,绝大多数公民,不管愿意与否,至少形式上都被吸纳到特定的社会团体和群众组织中,成为其中一员并受其制约,但权力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领导人通常由复兴党成员担任,并由政府任命或授意。一方面,这些社会团体和组织通过向统治者传达它们的意图和诉求,以实现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它们又在统治者的授意下实现特定的政治功能,即实现社会控制和政治动员。这更加充分说明了叙利亚国家的力量强大与政权的稳定之间的内在关联。此外,阿萨德政权在进行政策实施、意识形态宣传以及开展重大活动时,还通过社会团体和群众组织进行政治动员,以便获得民众的支持。在发生社会、政治动荡之时,政府又能通过武装那些亲政权的社会团体,孤立和镇压反对派。
阿萨德政治体制的特征
阿萨德执政后构建的政治体制,既不同于叙利亚独立初期脆弱的议会民主制,也不同于1963年至1970年复兴党执政初期建立的党军合一的政权形式。[31]阿萨德体制是叙利亚政治进程中的产物,但同时也是一种政治发展的过渡类型,它具有明显的新威权主义、少数派统治、世俗化政权等特征,这些特征深刻地影响着叙利亚的政治进程。
(一)新威权主义
新威权主义是阿萨德时期政治体制的显著特征。作为一种政治形态,威权主义政体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介于极权与民主政体之间的“较温和”的过渡型专制政体。其内涵是通过民主外壳下的威权手段进行强制性的权力控制和政治整合,以达到维持政治秩序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现代威权主义即新威权主义与传统威权主义的区别根源在于其合法性来源不同,新威权主义的合法性基础“不是靠传统的神圣性以及传统的规则和规范,而主要靠民族主义,以及‘奇里斯玛’人物的超凡魅力、独特禀赋和惊人的业绩等”,[32]统治者“能够以其个人的创造力、理论思想和政治实践,使国家的政治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甚至改变历史发展进程”[33]。阿萨德的政治体制产生于叙利亚民族独立运动和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中,是结束传统威权统治之后国家摆脱权威真空和政治衰朽的历史产物,其统治权威除了来源于阿拉伯民族主义与阿萨德个人魅力外,也通过其家族、亲信对军队、复兴党及政府官僚机构的控制等手段来实现。
新威权主义最突出的特征是对权力的控制、垄断和干预。同时,“政权的维系和发展是新权威主义政权的主要目标和任务,在这一过程中,政权除了继续依靠暴力和专制权力外,也开始强调诸如合法性、效能和有效性等支持政权基础的方面。”[34]阿萨德构建的体制是典型的新威权主义,在政治系统运作上,一方面,阿萨德实行强人政治和集权统治,将政治、经济、军事等大权集中在世俗的一人、一派、一党手中;另一方面,他借助于宪法、议会及进步阵线等形式赋予其权威统治以合法性,依靠军队、复兴党及官僚机构提高权力对社会的渗透和控制。庞大的国家机器以及压制性权力的频繁使用将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和自由限制在可控范围,致使政治反对派力量没有合法存在的空间,只能存在于体制之外。这便于排除或减少因政治竞争而带来的不确定性,但缺乏严格分权制衡的力量,也造成体制的僵硬和独裁。加之,这种体制缺乏畅通的政治参与渠道,社会公众的诉求不能通过政治参与的形式进行表达,往往会使社会矛盾得不到及时有效地化解,反而有可能酝酿、激化为突发的社会性危机。
(二)少数派统治
少数派统治多数派是阿萨德时期政治体制的第二大特征。叙利亚是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体的多民族多教派国家,长期以来,叙利亚政治、经济、社会的主导权掌控在逊尼派穆斯林精英手中,“自1930年以来,叙利亚的每一部宪法都规定国家元首必须是逊尼派穆斯林”。[35]阿萨德上台后,彻底结束了逊尼派主导叙利亚政治的局面。如前文所述,阿萨德主要依靠血缘、亲信等形成了一种统治国家的裙带网络和族裔势力,以此实现政治权力的集中,最终形成了少数统治多数的政治格局。“占全国人口12%的阿拉维宗教少数派,通过军事安全机构垄断了国家的最高权力,致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逊尼派穆斯林基本被排挤到权力体系边缘。”[36]
历史上,阿萨德所属的阿拉维派曾经长期处于被歧视受迫害的社会底层,曾经是毫无政治地位可言的社会阶层。阿拉维的含义是“阿里的崇拜者”,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一个小分支,除了遵循什叶派的基本教义外,也受到基督教的某些影响,该派还相信灵魂转世说,并保留对日、月、霞崇拜的残余。因此,阿拉维派自公元10世纪形成后一直被认为是异端。阿拉维派穆斯林生存状况非常恶劣,主要集中于拉塔基亚贫困的山区地带,历史上长期没有土地,沦为贫农、雇农或地主权贵的仆人。窘迫的生存环境和低下的社会政治地位,使阿拉维派穆斯林深藏着对翻身和复仇的渴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在叙利亚建立了委任统治。为防止叙利亚民族主义力量的联合,委任统治当局对叙利亚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利用阿拉维人长期以来对外界的不满情绪,利用其内部十分团结且英勇善战的民族精神,在政治上予以扶持,在经济上予以援助”[37],鼓励阿拉维派青年入伍参军,为他们提供武器装备。阿拉维派的历史发展也因此迎来了转机。法国委任统治当局曾组建了8个营的叙利亚新军,其中阿拉维营有3个,其他的部队里也有大量替主人服兵役的阿拉维仆人。由此,叙利亚军队就这样变成了阿拉维派的军队。1946年独立后叙利亚军队并没有进行深入的改造,加之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日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频频干政,甚至实施军事独裁,以及在历次的政治清洗运动中逊尼派军官逐步被排挤出军队高层,阿拉维派军人的政治地位和宗派主义成为复兴党人夺取国家权力的重要力量,更在阿萨德夺取政权的“纠正运动”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阿萨德上台后,为了提防逊尼派穆斯林的反叛,在国家政府关键部门大量安插阿拉维派亲信,于是,阿萨德政权演化为阿拉维派政权。“对于数千百年来一直在叙利亚占据统治地位的逊尼派穆斯林而言,作为少数派阿拉维派力量的得势是史无前例的震惊”,[38]因此,少数统治多数的特征成为威胁叙利亚国家政治进程的滥觞。
(三)世俗化政权
阿萨德政权具有明显的世俗化特征。世俗化是中东政教关系发展演变的总趋势。[39]“世俗化亦即政教分离过程,从实质上,它是指国家政治生活不受宗教的支配,政权的合法性不借助于宗教途径或神授性质。”[40]作为一个世俗的政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自1963年军事政变后,便开始在叙利亚实行世俗化的统治,包括穆斯林律法在内的各类宗教律法仅适用于境内各个宗教社群聚居地。阿萨德上台之后,政权的世俗性质进一步加强,世俗的政党与政府机构是权力的运作中心,阿拉伯复兴社会主义成为主导性的意识形态,伊斯兰教被置于国家政权的控制之下。1973年叙利亚宪法规定实行总统共和制,虽然为了减轻逊尼派穆斯林的敌意,阿萨德恢复了总统必须是穆斯林的条款,但宪法并不承认伊斯兰教的国教地位,叙利亚国家伊斯兰教的具体事务交由宗教基金部主管。
“所谓的世俗化往往与极权政治的膨胀表现为同步的状态,其实质在于极权政治自世俗领域向宗教领域的延伸。官僚化的教界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并未脱离政治领域和丧失政治功能,而是成为极权政治的御用工具。官方化的宗教学说则极力维护现存政治秩序的合法地位。”[41]这一论点在阿萨德体制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复兴社会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其创始人阿弗拉克便从伊斯兰教中寻找理论依据,他认为,“宗教和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是相统一的”,但并不认为“要把阿拉伯世界统一起来是以伊斯兰教为纽带,而是认为只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才能起到这种作用”。[42]阿萨德继承了这一思想,同时更具有实用主义趋向。一方面,他凭借政治权威进行世俗化改革,取缔和镇压穆斯林兄弟会等宗教反对派,并使宗教逐步远离政治,为复兴党的世俗化改革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他谨慎处理宗教与政治关系,吸纳逊尼派穆斯林进入权力高层,塑造政权的宗教合法性。因此,一些学者也将阿萨德的叙利亚看作是政教部分分离的国家。[43]但是伴随着现代化进程,阿萨德的政治体制世俗化倾向越发明显,招致国内宗教反对派和中东政教合一国家的强烈反对,严重威胁到政权的合法性。这在今日叙利亚的乱局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余 论
阿萨德构建的政治体制使叙利亚摆脱了独立后长期动荡的政治局面。尽管20世纪后期,中东政治风云变幻,但叙利亚仍然维系着政治稳定,在中东地区发挥着独特的政治影响力。从深层而言,阿萨德是通过权力的高度集中,特别是通过宗派和个人权威构建的威权制度来实现稳定的。阿萨德构建了阿萨德家族——阿拉维派——复兴党这样一个同心圆的权力架构,阿萨德个人权威在整个政治体系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这套制度虽然使叙利亚实现了稳定,但却是基于少数派统治多数派的制度。阿萨德并没有解决叙利亚独立以来民族国家构建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即如何在一个高度分裂型和冲突型的社会实现权力的相对平等、有效分配,而不只是通过威权统治的方式将社会隔阂掩盖起来。
2000年,巴沙尔上台后,继承了其父的政治体制,但未能延续其父的个人魅力与权威。故此,巴沙尔上台后便开始清洗复兴党中的元老和异己力量,培植个人亲信,树立个人权威。巴沙尔客观上削弱了复兴党对叙利亚社会的控制力。加之,在“九·一一”事件之后,叙利亚外部环境进一步恶化,美国推行的“大中东计划”也严重削弱了叙利亚的政治稳定。在巴沙尔并没有解决阿萨德体制的结构性矛盾而是使这套制度进一步弱化的情况下,叙利亚迅速卷入2010年末爆发的中东政治动荡中,陷入长时间的冲突直至全面内战。
然而,阿萨德体制也赋予了叙利亚不同于中东其他威权主义国家的属性。在中东变局中,突尼斯、利比亚、也门、埃及早已实现政权更迭,但叙利亚的巴沙尔政权依然坚挺,这与阿萨德体制密切相关。叙利亚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意识形态或社会阶层的冲突,而是不同派别的争夺。基于宗教少数派阿拉维派的巴沙尔政权控制了叙利亚的军队和政府,内部的凝聚力依然稳固。也正因为此,叙利亚现政权很难实现和平过渡,直至最终陷入内战泥潭。此次叙利亚危机与动荡在一定程度上使叙利亚政治进程回到了原点——分裂型和冲突型的社会。叙利亚未来将面对类似20世纪40年代独立初期的困境,即如何在不同教派和民族之间合理、有效地分配权力。在当代中东政治发展进程中,如何应对这一挑战还没有成功的先例,与叙利亚类似的伊拉克已经陷入国家分裂的边缘。当前的叙利亚危机只是叙利亚问题的第一阶段,未来一段时间内叙利亚将面临如何构建新制度的严峻挑战。
An Analysis on Syrian Political System at Asad’s Age
Wang Xingang & Ma Shuai
Abstract: From 1970 to 2000,Hafiz al-Asad set up the one-party presidentialauthoritarian political system by relying on the kinship,the tribes,thejanissary’s loyalty and hispersonal charms for as long as 30 years.Hemonopolized the political power in a very high degree with three major bases:militarysecurity departments,the Baath Party and the national bureaucracy.Asad’s political systemreflects such features as new authoritarianism,minority governance,secularizedregime,and etc, so the system is an outcome of a specific political process.However,Asad’s system hasn’t been able to solve the principle problems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the nation state since its independence,i.e. how to realize relative equality and effective distribution in ahighly divided and conflicted country. In 2000,Barshal succeededthe political system from his father, but th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 in thepolitical system remains unchanged.
Key Words: Political System; Syria; Hafiz al-Assad; Authoritarianism; BaathParty
(责任编辑:樊小红责任校对:詹世明)
[①]王林聪:《中东国家民主化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8页。
[②] [以色列]摩西·马奥茨著:《阿萨德传》,殷罡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42页。
[③]王新刚:《叙利亚现代政治发展影响因素分析》,载《西北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第153页。
[④]详见[美国]塞缪尔·P·亨廷顿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第175~181页。
[⑤] [美国]塞缪尔·P·亨廷顿:前引书,中译本序第5页。
[⑥]哈全安:《中东史:610~2000》,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58页。
[⑦]时延春:《中东风云人物》,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99页。
[⑧] [以色列]摩西·马奥茨:前引书,第31页。
[⑨] [以色列]摩西·马奥茨:前引书,第43页。
[⑩] Radwan Ziadeh,Power and Policy in Syria,I.B.Tauris,2011,p.16.
[11]姜士林、陈玮:《世界宪法大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版,第471~472页。
[12]王希:《阿萨德政治体制简析》,载《西亚非洲》2003年第3期,第56页。
[13] Hanna Batatu,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Social Roots of Syria’s Ruling,Military Group and the Causes for Its Dominance,Middle East Journal,Vol.35,No.3,Summer 1981,p.331.
[14] Eyal Lisser,Asad’s Legacy:Syriain Transition,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1,p.31.
[15]详见[以色列]摩西·马奥茨:前引书,第61页。
[16]严庭国:《当代叙利亚社会与文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85页。
[17] [以色列]摩西·马奥茨:前引书,第66页。
[18] Volker Perthe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yria under Asad,I.B.Turis,1992,p.147.
[19]姜士林、陈玮:前引书,第467页。
[20] Volker Perthes,op.cit.,p.155.
[21] [美国]乔尔·S·米格代尔:《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张长东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9页。
[22] Volker Perthes,op.cit.,p.141.
[23]王彤:《当代中东政治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2页。
[24]王新刚:《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51页。
[25] Volker Perthes,“Syria’s Parliamentary Elections:Remodeling Asad’s Political Base”,Middle East Report,Vol22,No.174,1992,p.18.
[26]严庭国:前引书,第70页。
[27]同上书,第68页。
[28]王新刚:《20世纪叙利亚:政治经济对外关系嬗变》,西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页。
[29]高光褔、马学清:《列国志·叙利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86~92页。
[30] John Galvani,Syria and the Baath Party,MERIP Reports,No.25,1974,p.10.
[31] Volker Perthe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yria under Asad,p.133.
[32]王林聪:前引书,第265页。
[33]王京烈:《动荡中东的多视角分析》,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246页。
[34]陈尧:《新权威主义政权的民主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页。
[35] [以色列]摩西·马奥茨,前引书,第59页。
[36] Yvette Talham,“The Syria Muslim Brothers and the Syrian-lranianRelationship”,Middle East Journal,Vol.63,No.4,Autumn 2009,p.561.
[37]王新刚:《20世纪叙利亚:政治经济对外关系嬗变》,第44页。
[38] Http://www.meforum.org/pipes/177/syria-after-asad,2015-08-12.
[39]陈德成:《中东政治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00页。
[40]王林聪:前引书,第188页。
[41]哈全安:《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58页。
[42]王新刚:《20世纪叙利亚:政治经济对外关系嬗变》,第165页。
[43]王京烈:《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55~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