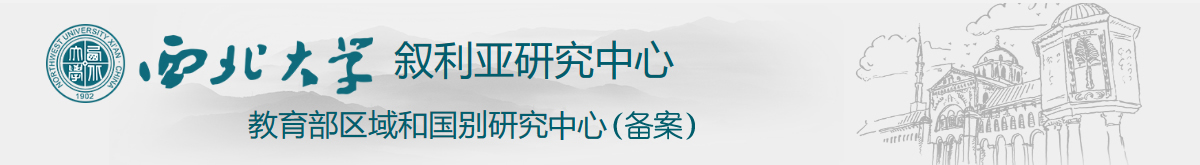阿富汗哈扎拉问题的历史嬗变与安全困境
[内容提要]:哈扎拉人是阿富汗第三大族群,也是阿富汗最为贫穷和边缘化的族群之一。阿富汗哈扎拉问题的历史嬗变与现实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段,其一是哈扎拉人抗拒阿富汗国家普什图化政策时期;其二是哈扎拉民族政治运动应对国家动荡时期(1979—2001)冲击的阶段;其三是当下哈扎拉民族在国家重建时期扮演的积极参与角色,以及要面对的族群安全问题阶段。重建时代的阿富汗国家基本消除了针对哈扎拉民族的不公正歧视和不平等政策,哈扎拉人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得到了显著提高。另一方面,阿富汗安全形势的不确定性成为了哈扎拉人群体安全的主要挑战,只有通过域内外各方势力共同推进的阿富汗和平进程,根除塔利班问题和“伊斯兰国”极端势力,才是解决阿富汗哈扎拉问题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 哈扎拉人;阿富汗;普什图人;塔利班
作者简介:杨玉龙,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安:710069)
哈扎拉人(Hazaras)是阿富汗第三大族群,哈扎拉民族文化拥有相当悠久的历史传统;与阿富汗其他族群不同的是,哈扎拉人在历史上皈依了什叶派信仰,接纳了波斯语言文化作为母语,其宗教与民族文化和伊朗有天然的联系。以历史范畴而论,哈扎拉人是阿富汗国内最为贫穷和边缘化的族群之一,数百年以来被阿富汗主体民族歧视和同化,因此哈扎拉人在阿富汗社会中处于非常劣势的社会经济地位,在阶层分化中大多位于农民和手工劳动者等服务业的社会低下职业,生活境遇相当贫苦。
2001年阿富汗战争后,后塔利班时代的阿富汗进入国家重建时代,哈扎拉民族在国家政治和重建时期扮演着日益重要的积极角色。由于阿富汗社会多元的族群、教派特征,主体民族普什图人在人口结构和民族分布中并不占优势;同时,阿富汗特殊的地缘条件使其百年来成为大国博弈的地缘角力场,“大博弈”的外部干预和脆弱的内部社会凝聚力使阿富汗自19世纪以来历经若干大国的军事入侵或颠覆,缺乏国家建构的政治权威和强政府传统。因此,后塔利班时代的哈扎拉民族对阿富汗政治将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而哈扎拉民族与普什图民族的族际关系将成为影响阿富汗社会稳定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研究阿富汗哈扎拉问题的历史嬗变和现实挑战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
本文将结合现代阿富汗政治发展与哈扎拉问题的历史变迁,从现代阿富汗国家政治发展、动荡和转型的视角审视哈扎拉问题不同历史阶段的主要特征和历史内涵,分析阿富汗政治发展进程对哈扎拉问题的深刻影响,并结合现实要素概述当下哈扎拉问题的主要挑战。
一、阿富汗哈扎拉问题的历史起源
(一)阿富汗哈扎拉民族的概况和特征
阿富汗的2700万人口由诸多族群组成,其中普什图人(Pashtuns)、塔吉克人(Tajiks)、哈扎拉人分别占总人口的42%、25-30%、10%,是人口最多的三个族群。根据“皮尤论坛宗教和公共生活”(The Pew Forum on Religion &Public Life)2009年的调查报告显示,阿富汗哈扎拉人大约300万到400万。哈扎拉人的语言为阿富汗波斯语或称达利语(Dari),哈扎拉人中大部分信仰伊斯兰教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分支,少数哈扎拉人信仰什叶派伊斯玛仪分支,另有极少量哈扎拉人属于逊尼派信仰。
哈扎拉人居住在阿富汗中部地区,该地区传统上被称之为“哈扎拉贾特”(Hazarajat),包括巴米扬(Bamiyan)、加兹尼(Ghazni)、乌鲁兹甘(Uruzgan)、古尔(Ghor)等省份,哈扎拉人还聚居在喀布尔市的西区;而20世纪末阿富汗持续的战乱导致许多哈扎拉难民逃亡至临近的巴基斯坦和伊朗。
阿富汗哈扎拉民族的特征可以概括为部落、族体、宗教、文化四个方面。其一,哈扎拉民族的传统社会结构以部落为基本组织形式,在哈扎拉贾特6省 中有数个哈扎拉部落,彼此互不统属。其二,哈扎拉族体特征表现为混合性。哈扎拉人的族源问题在民族学、人类学界一直存在争议,包括蒙古起源论、混合起源论、本土起源论多种说法。目前学术界倾向于混合起源论观点,即哈扎拉人的族源包括了阿富汗中部土著人、蒙古人、突厥人等多种血缘。其三,哈扎拉民族主体信仰伊斯兰教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支派教义。哈扎拉人大约13世纪前后定居于阿富汗中部哈扎拉贾特,S.A.穆萨维(S.A.Mousavi)认为哈扎拉人皈依什叶派的时间始于13世纪伊尔汗国合赞汗和阿布·萨义德时期,16世纪萨法维王朝阿拔斯一世时期完成。其四,哈扎拉民族文化融合了波斯、阿富汗、中亚等多元地域的文化内涵,属于混合型民族文化特征。就哈扎拉民族心理倾向而论,哈扎拉人与伊朗波斯文化具有一定向心力,彼此的语言、习俗、宗教等存在高度相似性。不过,近数十年来阿富汗社会的城市化和政府普什图化政策,使哈扎拉民族文化日益分野为普什图化(Pashtunized)和波斯化(Persianized)两种方向的文化更新。
(二)阿富汗王国的中央集权化与普什图化政策的确立
19世纪后期阿富汗国家进入中央集权化阶段,阿卜杜·拉赫曼埃米尔(Abdul Rahman
Amir)对地方部落、少数族群实施政治控制策略,试图构建统一的、以普什图族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国家。当时的哈扎拉贾特基本由地方部落酋长和宗教谢赫领导,阿富汗王国政府对该区域仅存在象征性的统治。哈扎拉民族地域内部以部落为单位形成互不统属的权力分散型社会。
哈扎拉民族地域的社会结构以部落为基本单元,统治阶级是部落大地主贵族,其头衔主要是米尔(Mir)等。传统社会的哈扎拉人是依附于地主贵族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社会关系依靠部落权威和宗教领袖调整。哈扎拉人的土地贵族和阿富汗国王的关系基于相互合作原则,哈扎拉米尔代表国王征收税收,保护境内商路安全,发生战争时向国王提供家族和部落武装,国王向米尔们给予授权在各自地区行使政治权力作为回报。
阿卜杜勒·拉赫曼埃米尔试图加强中央集权化的政策打破了喀布尔与哈扎拉贾特之间传统的政治平衡,引发哈扎拉人的激烈反抗。阿卜杜勒·拉赫曼埃米尔以哈扎拉人的抗税斗争为契机,以军事弹压手段消弭抗税斗争,借机将中央政府军队派驻至哈扎拉贾特,以国家权威和政治控制实现对哈扎拉贾特的直接统治。1889年,阿卜杜拉·拉赫曼向向哈扎拉人征收惩罚性重税,引发哈扎拉人部落的抗税起义。
阿卜杜勒·拉赫曼埃米尔镇压了哈扎拉人起义后,对哈扎拉贾特推行中央集权化和普什图化政策,以分而治之策略和民族、宗教同化策略为手段。首先,哈扎拉贾特的行政区划被分解并入喀布尔、巴米扬和坎大哈三省,以政治地理的行政区划重构方式对哈扎拉人聚居区推行分而治之策略。其次,以高额税收方式惩罚哈扎拉人的反政府行动,导致大量哈扎拉人家庭破产或逃离哈扎拉贾特。再次,政府在哈扎拉贾特强制推行逊尼派信仰和普什图语言文化,派遣逊尼派宗教人员前往哈扎拉贾特村庄,强迫哈扎拉居民放弃什叶派信仰,必须在逊尼派清真寺做礼拜。阿卜杜勒·拉赫曼埃米尔命令喀布尔的乌莱玛发布法特瓦,宣布哈扎拉人为异教徒,打压哈扎拉人宗教信仰的合法性。最后,阿卜杜勒·拉赫曼试图强制改变哈扎拉贾特传统的民族结构,在哈扎拉贾特西南部迁徙普什图游牧民定居。
阿卜杜拉·拉赫曼埃米尔时期的哈扎拉政策及其举措对哈扎拉民族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其一,战争对哈扎拉贾特造成严重的经济重创,哈扎拉难民群体被迫移民至周边国家,进而形成了伊朗和巴基斯坦的哈扎拉移民社群。其二,宗教与民族同化政策引起哈扎拉人的抗拒心理,反向促进了哈扎拉人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和族体内部团结,强化了哈扎拉人的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正如哈扎拉问题研究学者博达利·哈桑(Podali Hassan)评价:“这场战争的遭遇使哈扎拉人创造了更强的统一意识。”
穆罕默德·纳迪尔沙阿(Muhammad Nadir Shah)继任后恢复了阿卜杜·拉赫曼时代的哈扎拉政策,对哈扎拉贾特实施普什图化(Pushtunizaiton)策略。纳迪尔委任的哈扎拉贾特总督在当地推行去哈扎拉化政策,要求哈扎拉人接受普什图语言和文化,弱化哈扎拉人的历史记忆,更改哈扎拉贾特传统地名,禁止传播哈扎拉民族历史和文化。纳迪尔的哈扎拉政策引发哈扎拉民族主义者的报复,1939年纳迪尔被哈扎拉人阿卜杜勒·卡里克(Abdul Khaliq)派人刺杀。
(三)二战后阿富汗国家现代化与哈扎拉民族主义的泛起(1945—1979)
二战结束后阿富汗国家迈入现代化时期,哈扎拉人在民主政治参与等方面有一定进步,但社会经济、大众教育等方面仍很落后。以大众教育为例,战后阿富汗建设国家教育体系,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有一定发展,但哈扎拉人分享到的国家教育资源极为有限。50至60年代阿富汗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大部分哈扎拉学生无法进入大学学习,许多哈扎拉学生只能选择接受传统宗教教育。
二战后阿富汗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推动了社会经济发展和高等教育的普及,自由主义的改革措施也促使哈扎拉民族发展出不同思想倾向的政治运动,包括伊斯兰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等思潮在哈扎拉知识分子中间深入传播。
1963年查希尔国王亲政,阿富汗进入“十年宪政”时期。查希尔亲政后推动新宪法的制定,重建阿富汗君主立宪政体。1964年9月喀布尔的国民大会经国王批准通过新宪法,阿富汗进入宪政时代。政治改革推动了哈扎拉人的政治自由化和政治参与,哈扎拉人代表被任命为内阁成员,哈扎拉贵族被选进阿富汗参议院、众议院。哈扎拉人还建立了政治组织“进步青年会”(Progressive Youth Organization),其意识形态是左翼思想的毛派组织,对哈扎拉穆斯林中的劳工阶层很有影响。
这一时期哈扎拉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哈扎拉民族主义推动了哈扎拉人改变本民族地位的强烈诉求。哈扎拉民族主义代表向阿富汗国家提出了改变哈扎拉人社会地位的要求,其一是要求阿富汗宪法承认什叶派十二伊玛目信仰的合法性,取得与逊尼派信仰平等的宗教地位;其二,结束数百年来对哈扎拉人的民族歧视,停止普什图化政策;其三,给予哈扎拉人平等的受教育权利,改变哈扎拉贾特贫穷落后的社会经济境况和落后的基础教育。
1973年达乌德发动政变推翻查希尔国王统治,阿富汗进入共和时期(1973-1978),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在苏联支持下势力发展迅速,1977年党内两派旗帜派与人民派恢复合作与党内统一,1978年4月人民民主党发动“四月革命”推翻了达乌德政权,人民民主党建立亲苏政府,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Noor Mohammad Taraki)成为政府首脑。人民民主党政权建立后阿富汗国内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政治稳定面临各派势力挑战,人民民主党的对内政策是引发国内政治动荡的重要因素。塔拉基政府上台后对包括哈扎拉人在内的少数族群实施严厉的限制政策,进而引起各个少数族群的强烈反弹。1979年4月哈扎拉贾特古尔、巴米扬、乌鲁兹甘省掀起反政府的哈扎拉人政治运动。
二、苏联入侵和塔利班统治时代哈扎拉民族的抵抗运动
(一)苏联侵略阿富汗与哈扎拉抵抗运动
1979年9月,哈菲祖拉·阿明(Hafizullah Amin)通过政变取代塔拉基,阿富汗政治局势日益复杂化和动荡,由于地方各派势力的圣战运动愈演愈烈,中央政府已经失去对哈扎拉贾特的控制,哈扎拉人各派势力忙于政治联合,亲伊朗的哈扎拉人政治组织开始活跃起来。12月24日,苏联军队空降喀布尔,阿明政权被苏联通过军事政变推翻,人民民主党的巴布拉克·卡尔迈勒(Babrak Karmal)由苏联扶持为阿富汗总统。
1979年,哈扎拉民族政治势力聚集在哈扎拉贾特巴米扬省,建立“阿富汗伊斯兰联盟委员会”(Islamic Council of Union in Afghanistan, ICUA),目标是团结普什图民族,反抗苏联对阿富汗的干涉和入侵。伊斯兰联盟委员会选举赛义德·阿里·贝希什提(Sayed Ali Behishiti)为主席,联盟拥有数千名军事人员,委派阿富汗前国王查希尔的军队将领赛义德·贾格兰(Sayed Jagran)指挥,军事活动区域主要围绕加兹尼、巴米扬、和巴尔赫省份。
卡尔迈勒执政时期哈扎拉人加入反苏联入侵的圣战运动,成为抵抗苏联入侵的阿富汗各派势力之一。1980年2月,喀布尔哈扎拉人因抗议喀布尔政府发动示威游行,各派组织发动“赛胡特起义”(Insurrection of Se-e-Hoot),起义参与者主要为喀布尔哈扎拉人居民,抗议者包围苏联驻阿富汗大使馆,攻击前总统阿明的住所和警察局。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革命卫队(Revolutionary Guards,RG)对赛胡特起义实施以强硬镇压措施。
新生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积极介入阿富汗反苏联入侵的圣战者运动,哈扎拉人的民族政党与伊朗建立了密切联系。伊朗支持贝希什提领导的阿富汗伊斯兰联盟委员会,通过外部军事支持和经济援助帮助伊斯兰联盟委员会打击苏联军队和人民民主党政权。1987年9月,伊朗帮助在其境内流亡的8个哈扎拉民族政治组织建立“阿富汗伊斯兰革命联盟”(Islamic Revolutionary Union of Afghanistan,IRUA),即所谓的“八党联盟”。
1986年5月,苏联政府以纳吉布拉取代卡尔迈勒就任阿富汗总统和人民民主党总书记,纳吉布拉政权在圣战运动打击下已经摇摇欲坠。1986年末,纳吉布拉提出全国和解计划,未取得圣战运动组织认可,全国和解计划陷入僵局。1988年,苏联政府提出撤军计划,至此人民民主党政权已经失去依靠,1989年2月苏联军队撤出阿富汗,喀布尔政府在圣战组织打击下统治区域不断缩小,至1992年垮台。
(二)哈扎拉民族政党在内战中的角逐和族际暴力冲突(1992-1996)
苏联解体之际,阿富汗国内政治与军事格局产生了根本性改变,由于苏联政府撤出了在阿富汗的驻军,逐渐断绝了对阿富汗纳吉布拉政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阿富汗国内脆弱的政治和军事平衡被打破,各派政治与军事势力重新分化组合,阿富汗陷入更加混乱的内战阶段。
势力分散的阿富汗国内哈扎拉人政党和军事派别逐渐联合为统一性的政治力量,以此与其他派别政治联盟抗衡。1989年2月,阿富汗反政府逊尼派组织联盟在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建立“过渡政府”,但“过渡政府”将哈扎拉民族政党排除在外。1989年中,阿富哈扎拉人各派政党和武装派别结成统一的政治联盟——“阿富汗伊斯兰团结党”(Islamic Unity Party of Afghanistan,IUPA),党主席为阿卜杜拉·阿里·马扎里(Abdul Ali Mazari)。
人民民主党政权垮台后,阿富汗国内已不存在能够有效维持政治稳定和军事冲突控制的政治力量,普什图、塔吉克、哈扎拉三族的各派政治和武装力量竞相争夺政治领导权和领土控制,当时的阿富汗实质上已陷入军阀混战的内乱状态,普什图、塔吉克等逊尼派政治集团和哈扎拉人伊斯兰团结党的政治分歧难以弥合,两派政治分歧和矛盾冲突背后还暗含着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地区博弈的深刻根源。
这一时期阿富汗军阀混战的聚焦点是对中央政府权力分配和喀布尔城区的争夺,伊斯兰团结党与普什图政党、塔吉克政党之间产生了政治利益冲突和政见分歧,沙特与伊朗的地区博弈加剧了哈扎拉政党与其他两大民族政党集团的矛盾,进而引发了持续性的军事冲突和针对哈扎拉平民的集体暴力惨剧。1992年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西区先后爆发多次普什图人、塔吉克人武装与伊斯兰统一党的武装冲突,双方共发生战斗27次,是当时喀布尔军事冲突次数最多的区域。
1993年“阿夫沙尔事件”(Afshar Event)是阿富汗内战期间普什图、塔吉克军阀针对哈扎拉民族的集体屠杀行动,该事件反映了战乱时期阿富汗国内已严重恶化的族际关系和日臻白热化的政治派别冲突,哈扎拉民众沦为了军阀混战牺牲品。阿夫沙尔是喀布尔西部街区,聚居居民主要是哈扎拉什叶派。1993年初,拉巴尼、马苏德等普什图和塔吉克军阀试图夺取伊斯兰团结党控制的喀布尔西区,故发动“阿夫沙尔行动”(Afshar Operation)的军事作战计划,军事行动失控后演变为针对性屠杀哈扎拉什叶派的惨剧,约700名哈扎拉人死于阿夫沙尔事件。
阿夫沙尔事件后,阿富汗国内的军阀混战状态有增无减,塔利班势力泛起改变了军阀混战的政治格局,哈扎拉人的少数族群特征和什叶派信仰属性成为塔利班武装首要的打击目标,1995年伊斯兰团结党主席马扎里和其他党内核心成员被塔利班武装集体处决,哈扎拉民族政党转入低潮期,哈扎拉人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危机。
(三)阿富汗塔利班势力对哈扎拉人的恐怖政策
1992年阿富汗内战爆发后,塔利班在混乱的政治局势中异军突起,塔利班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普什图民族主义为旗帜联合了一批政治力量,在阿富汗南部地区发展迅速。1996年塔利班夺取喀布尔后,在阿富汗国内建立逊尼派原教旨主义思想主导下的政治统治。塔利班政权对国内的宗教少数派和少数民族实施各种形式的迫害政策,哈扎拉贾特陷入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对塔利班政权而言,对哈扎拉人实施恐怖政策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的考量。其一,哈扎拉民族政党与塔吉克、乌兹别克等族的军事力量是塔利班政权对阿富汗全国确立统治地位的主要障碍,恐怖政策可以震慑哈扎拉人,削弱伊斯兰团结党等反抗势力。其二,塔利班的宗教意识形态将什叶派认定为罪恶的“异教徒”,哈扎拉人的什叶派信仰是塔利班无法容忍的“异端”存在。其三,塔利班背后的极端民族主义倾向也将仇恨心理指向哈扎拉等少数族群。因此,塔利班统治阿富汗时期的哈扎拉民族遭遇了百年来最为严峻的生存危机和安全困境,塔利班的集体暴力行动使哈扎拉人的生命境况一度恶化至人道主义危机。
塔利班政权建立后,伊斯兰团结党以哈扎拉贾特的巴米扬省为根据地,与与拉巴尼、马苏德、杜斯特姆等普什图、塔吉克、乌兹别克族武装联合对抗塔利班政权。1996年伊斯兰团结党加入阿富汗其他各族组建的“拯救阿富汗全国伊斯兰统一阵线”(National Islamic United Front for the Salvation of Afghanistan,NIUFSA),联盟的主要目标是推翻塔利班政权。
马扎尔沙里夫事件(Mazar-i Sharif Ethnic Massacre)是塔利班针对哈扎拉民族犯下最严重的暴力罪行。1998年8月塔利班军队再次占领马扎尔沙里夫,塔利班武装占领马扎尔沙里夫城市后对市内的哈扎拉居民采取无差别形式的军事攻击,保守估计约有2000多人遇难。1998年9月13日,塔利班军队进入哈扎拉人聚居的巴米扬省,50多名哈扎拉平民被杀。
三、后塔利班时代哈扎拉人对国家政治的参与和族群安全挑战
2001年“9·11事件”改变了阿富汗国家历史进程,也成为阿富汗哈扎拉民族命运重要的转折点之一。“9·11事件”引发美国及其西方同盟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战争,阿富汗战争瓦解了塔利班势力对全国的统治,哈扎拉民族得以摆脱塔利班政权的残酷统治,后塔利班时代的哈扎拉民族以平等地位和积极参与的角色投身于阿富汗的国家重建进程之中。在《波恩协议》(Bonn Agreement)和阿富汗宪法的保护下,卡尔扎伊政府积极实施保护少数族群和宗教少数派别的国家政策。
2001年阿富汗战争结束后,哈扎拉民族政党发表了《民族宣言》(Declaration of a People),哈扎拉人寻求在阿富汗国家重建进程与国家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该宣言反映出哈扎拉人追求平等公民权利、和谐族际关系与教派关系的意愿,其中心思想是控诉近两百年来阿富汗哈扎拉民族遭受的不公正对待和血泪的集体记忆。
哈扎拉民族在后塔利班时代阿富汗国家重建中的地位和角色,可以从宪法等国家法律文本、民主政治参与、宗教平等地位三个方面予以考察。总体而论,哈扎拉民族基本挣脱了数百年以来不断强化的民族不平等地位,赢得了平等公民权和宗教信仰自由;以主动参与的姿态加入了阿富汗民主政治体制的构建和运行,在阿富汗国家政治走向中扮演了积极角色,哈扎拉民族政党在国家政治层面与中央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合作机制,参与了国会选举和政党政治,在哈扎拉人聚居区的地方政治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和民族地方的行政自治功能。
首先,阿富汗国家新宪法和其他法律给予了哈扎拉民族平等公民权和保护少数族群的
特别政策。2004年阿富汗新宪法给予国内所有民族和宗教少数派平等公民权,哈扎拉人什叶派公民有权申请以什叶派教法处理家庭事务。
其次,哈扎拉民族积极参与战后阿富汗的民主政治重建,许多哈扎拉政治家成为国家
行政、立法等机构的高级官员。其一,哈扎拉政治家积极参与阿富汗国家政治。立法机构方面,2010年阿富汗议会下院选举,249个席位中哈扎拉代表当选59人;2011年阿赫马德·拜扎德(Ahmad Behzad)担任议会下院议长。伊斯兰团结党主席卡里姆·哈里里(Karim Khalili)曾担任卡尔扎伊时期的副总统,卡尔扎伊总统内阁阁员中哈扎拉人曾一度多达5人。
其二,哈扎拉民族政党积极加入阿富汗国家的政党政治,卡里姆·哈里里领导的伊斯兰团结党是代表哈扎拉民族利益的主要政党,在阿富汗议会中拥有强劲的影响力。穆罕默德·莫哈基克(Muhammad Mohaqiq)领导的“阿富汗哈扎拉人民伊斯兰统一党”(Hazara People`Islamic Unity Party of Afghanistan,HPIUPA)是阿富汗议会中新兴的哈扎拉人政党。
其三,哈扎拉人政治家以相对的行政自主权力领导和参与哈扎拉人民族地方治理,担任哈扎拉贾特各省的省长和地方官员,如哈扎拉族著名的政治家哈比巴·索拉比(Habiba Sorabi)等。2004年阿富汗政府从巴米扬省中划出哈扎拉人聚居区为代昆迪省(Daikundi Province),扩大哈扎拉人地方行政的自主性。
再次,2009年阿富汗议会通过《什叶派个人地位法》(Shia Personal Status Law),正式以国家立法形式进一步确保了哈扎拉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什叶派宗教领袖谢赫·莫赫塞尼(Sheikh Mohseni)曾担任卡尔扎伊总统的宗教顾问。
2012年以来,阿富汗国内安全局势再次恶化,哈扎拉民族面临着严重的群体安全挑战。2012年,阿富汗塔利班武装的活动范围发生了较大程度的变化,在此之前塔利班武装的传统政治基础来自于阿富汗南部和东南部省份的普什图部落地区;2012年后,塔利班武装的战略目标转移至阿富汗的北部和西部省份,这些区域聚居着塔吉克、乌兹别克和哈扎拉人等少数族群。历史上,哈扎拉民族和塔利班组织之间有深厚的历史积怨和冲突记忆,特别是塔利班的意识形态与哈扎拉人的什叶派信仰有着一定程度对立,塔利班武装进入阿富汗中部后,将哈扎拉人聚居区作为袭击目标的重点。
塔利班武装活动范围和战略目标转移的主要原因为两点。其一,阿富汗北部和西部等区域的政府安全力量较为薄弱,美国等西方国家驻扎的军事存在相对不足,这一安全格局给予了塔利班武装扩大活动范围,占据农村地区等势力范围的条件。其二,阿富汗民族团结政府(National Unity Government, NUG))秉持普什图民族主义倾向,阿什拉夫·加尼(Ashraf Ghani)政府缺乏对哈扎拉等少数族群聚居区域提供集体安全保护的主观意愿。2018年10月,塔利班武装袭击了居住在阿富汗中部乌鲁兹甘省(Uruzgan Province)和加兹尼省(Ghazni Province)的哈扎拉居民,造成100多名哈扎拉人死亡,1000多人被迫离开居住地寻求安全保护。
阿富汗哈扎拉人成为“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武装分子发动袭击的目标之一。2018年11月12日,“伊斯兰国”袭击了喀布尔市哈扎拉人,造成6人死亡和多人受伤。 “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声称数千名哈扎拉人参与了伊朗的叙利亚危机军事干预行动,极端分子将哈扎拉人的聚居区、清真寺、圣地、圣墓等建筑物或地点作为袭击目标。对于“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而论,发动对哈扎拉人的军事袭击行动,其主要战略目标是削弱伊朗在阿富汗的利益。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伊朗对阿富汗问题保持了长期的介入政策,积极支持哈扎拉什叶派和塔吉克人,伊朗在阿富汗西部赫拉特等区域存在密切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由于长年战争和动乱,阿富汗哈扎拉人和塔吉克人难民多选择伊朗作为避难国家;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伊朗应叙利亚政府邀请,以军事援助和介入手段支持巴沙尔政府的正面战场。由此,近年来“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将哈扎拉人列为主要的袭击目标,以此削弱伊朗在阿富汗的利益,或以暴力袭击方式“惩戒”哈扎拉民族与伊朗之间的密切往来。
哈扎拉人群体安全的威胁主要根源是阿富汗国家缺乏有效的安全保障机制和社会秩序维持能力。目前,阿富汗全国仍有近50%的领土在塔利班武装势力影响下,部分农村地区被塔利班实际控制。虽然美国等为首的西方国家在阿富汗拥有长期的军事力量存在,其实际控制能力有相当的局限性,阿富汗政府军也无力以军事手段压制或弱化塔利班武装存在,阿富汗问题的和平建设仍悬而未决。由于阿富汗国家安全的半真空状态和脆弱的安全保障机制,哈扎拉人仍将长期面对塔利班、“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的安全威胁,频繁的暴力袭击事件造成了不可逆的多重影响。
其一,频繁的暴力袭击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阿富汗国内的族际冲突。多元族群的现实存在和历史上的多发性族际冲突使阿富汗国内存在着一定张力的潜在族际矛盾,族际关系的不稳定是威胁阿富汗政治稳定与发展的主要变量之一。哈扎拉人与普什图民族间的历史积怨和政治歧见极易被塔利班组织利用,虽然塔利班组织的意识形态以宗教极端主义为主,也不能掩盖其显著的极端民族主义倾向。
其二,针对哈扎拉人的集体暴力袭击也体现了教派冲突的特征。哈扎拉人成为塔利班和“伊斯兰国”袭击目标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教派矛盾,哈扎拉人大部分信仰什叶派教义,与伊朗有着深厚的宗教情感联系,哈扎拉民族的什叶派宗教属性成为塔利班等宗教极端组织表现其意识形态的政治工具,从而加剧了教派冲突的现实和教派主义话语。
阿富汗哈扎拉民族面对塔利班武装的频繁袭击以及地方安全真空现实,以自组织形式建立民兵武装“人民保卫军”(People`s Defense Forces, PDF)。人民保卫军最早建立于哈米德·卡尔扎伊(Hamid Karzai)政府时期,由阿富汗国防部直接管辖,负责保卫地方村镇安全;加尼执政后,国防部与人民保卫军脱离关系,人民保卫军失去政府支持和经济资助,演变为地方性的自组织形式民兵武装。但是,人民保卫军的力量毕竟有限,2018年11月塔利班武装对哈扎拉人的暴力袭击未能得到有效遏制,哈扎拉人面临的群体安全困境依然存在,乌鲁兹甘省等地的哈扎拉民众只能寻求美国、澳大利亚等部队的安全庇护。
当前,哈扎拉民族的群体安全保护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其一是阿富汗政府提供的军事安全保护;其二是自组织形式的民兵武装;其三是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提供的军事安全。澳大利亚是全世界范围内接收哈扎拉难民最多的国家,同时在阿富汗境内驻扎了人数仅次于北约的军队,并为阿富汗军队提供军事培训和装备。
四、结论
从历史纵向角度审视阿富汗哈扎拉问题的历史嬗变与现实,可以把被边缘化的哈扎拉民族不懈地追求民族平等权利的历史进程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段。其一是哈扎拉人抗拒阿富汗国家普什图化政策时期;其二是哈扎拉民族政治运动应对国家动荡时期(1979—2001)冲击的阶段;其三是当下哈扎拉民族在国家重建时期扮演的积极参与角色,以及要面对的族群安全问题阶段。
现代阿富汗国家现代化进程对哈扎拉族群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中央集权化和普什图化政策形成了对哈扎拉民族文化和民族认同的强烈冲击,刺激了哈扎拉人的抗拒心理和民族意识;另一方面,现代化进程催生了现代哈扎拉民族主义思潮,加强了哈扎拉民族团结,哈扎拉人的什叶派属性还受到伊朗霍梅尼主义宗教政治思想的浸染,因而哈扎拉人抗拒普什图化政策的民族思潮内核包含了民族和宗教双重特征。阿富汗国家动荡的二十年是哈扎拉人从国家边缘走向政治中心舞台的转折时期,哈扎拉人受阿富汗国家认同的影响,积极参与抵抗苏联入侵的圣战运动;在伊朗的外部支持和民族团结内部凝聚等因素影响下共生出第一个统一性的哈扎拉民族政党——伊斯兰团结党。阿富汗国家动荡衍生出军阀混战和原教旨主义的塔利班势力,先后制造了阿夫沙尔事件和马扎尔沙里夫事件等屠杀哈扎拉平民的历史惨剧,这一时期不仅是阿富汗现代历史上最为动荡和混乱的内战状态,也是阿富汗国内族际冲突和族际暴力最剧烈和频繁的特殊时期。2001年阿富汗战争极大地改变了哈扎拉人民族历史的轨迹,哈扎拉人以平等的公民身份参与后塔利班时代的阿富汗重建进程,阿富汗新宪法和其他国家法律文本给予了哈扎拉人平等的民族地位和公民身份,充分肯定了什叶派信仰的合法性。哈扎拉人在阿富汗国家政治中扮演了积极参与的角色,有效地在议会、政党政治、地方政治发挥了政治建设作用。重建时期阿富汗国家政治推行的权力分配体制弥合了各族群间的政治分歧,促进了阿富汗主要族群间的和谐关系。
另一方面,阿富汗安全形势的不确定性成为了哈扎拉人群体安全最主要的挑战。哈扎拉人族群安全的威胁来自于塔利班武装和“伊斯兰国”,近年来塔利班改变了在阿富汗国内的战略重点和目标,哈扎拉贾特和哈扎拉平民成为了塔利班武装袭击的重要对象;“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也将哈扎拉人作为“异教徒”而频繁发动暴力袭击。哈扎拉人的族群安全问题已成为阿富汗安全形势困境主要的表征之一,随着近年来美国驻军的减少,塔利班在阿富汗境内重新扩大了盘踞控制区域,哈扎拉贾特已陷入四面包围的困境;而“伊斯兰国”极端势力泛起加剧了哈扎拉人的群体安全困境。
虽然阿富汗政府和美国等国际军事力量提供了部分安全保护机制,但是哈扎拉人的族群安全依赖于外部的军事保护不能根除其群体安全困境的根源,阿富汗塔利班武装的存在和“伊斯兰国”极端主义组织的泛起将长期性的成为哈扎拉人族群安全的主要威胁,只有通过域内外各方势力共同推进的阿富汗和平进程化解塔利班问题,根除“伊斯兰国”极端主义势力及其思潮,才是彻底解决阿富汗哈扎拉问题的充要条件和必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