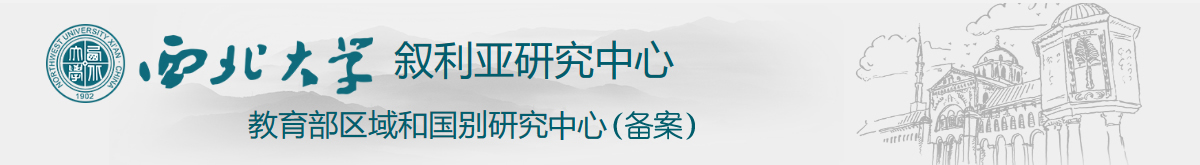当地时间8月13日,当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以色列和阿联酋宣布签订和平协议的时候,似乎终于扯下了一片中东地缘政治的遮羞布。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的接触,终于从“公开的秘密”走向了“公示于众”。民族主义的浪潮,最终逐渐击败了曾席卷中东的“泛阿拉伯主义”思想。巴以问题的边缘化,也许是历史演进的必然的结果。
阿联酋和以色列之间缔结和平条约,很容易使人联想到1979年以色列和埃及缔结和平条约,以及1994年以色列和约旦缔结和平条约。阿联酋也成为了继埃及和约旦之后,第三个与以色列缔结和平条约的阿拉伯国家,也成为了第一个与以色列建立正常关系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历史总有很多相似,相似之处,也见证着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埃及与以色列的和解,不少人一度怀疑这是萨达特“圈套”
1979年,以色列和埃及缔结和平条约,象征着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关系的重大转折。实际上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时任埃及领导人的萨达特,就已经在反思与以色列的关系。埃及长期处于与以色列对抗的最前沿,从第一次中东战争到第四次中东战争,埃及曾收获了无限的荣光,也失去了几乎所有的尊严。第一次中东战争,让埃及民众对于腐败的王国政治失去信心,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埃及革命的爆发。第二次中东战争,纳赛尔领导埃及军民抗击英国、法国和以色列的联合入侵,一跃跻身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阿拉伯民族主义浪潮也席卷了整个中东。第三次中东战争,让埃及颜面扫地,纳赛尔的政治话语不再拥有迷人的魅力,伊斯兰政治理念也开始以更加激进的形态在埃及蔓延。第四次中东战争,埃及先胜后败,也意识到了无法消灭强大的以色列,只能通过其他路径来寻求突破。
数十年的冲突和战争,给埃及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政府财务不得不向军事大幅度倾斜,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社会矛盾。埃及所仰仗的苏联,只是将埃及作为一个战略棋子,在关键的时刻屡屡“掉链子”,对于埃及亟需的各类军事装备总是犹犹豫豫不愿提供。即使是那些信誓旦旦表示与埃及共同抗击以色列的“阿拉伯兄弟们”,也总是在关键时刻或是“看热闹”,或是“有心无力”。那些与以色列距离越远的阿拉伯国家,总是叫嚣的嗓门最亮。埃及这个阿拉伯世界“领袖”,再也无力承担与以色列的战争消耗,因此选择改换门庭,同美国发展友好关系,同时促成了与以色列的和解。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梦想后,埃及终于抛弃幻想,转而尊奉“国家利益”优先的原则,大胆的走出了第一步。
埃及与以色列的和解,一度让以色列不知所措。数十年的死敌,突然放下武器发展正常关系,让以色列难以相信。即使是萨达特在1977年飞往耶路撒冷时,以色列高层仍然有不少人怀疑这是萨达特“圈套”,有人认为飞机中是当时以色列定义的恐怖分子、巴勒斯坦解放运动领导人阿拉法特而不是萨达特,其目的是为了羞辱以色列;也有人甚至信誓旦旦的拿出“据可信的情报”显示,飞机上是埃及的“敢死队”,其目的就是为了杀死欢迎萨达特的以色列领导人,然后埃及大军在边境上发动突袭。有趣的是,当时与埃及恢复邦交关系的,正是长期被视为以色列强硬派的利库德领导人、时任以色列总理梅纳海姆·贝京。
约旦与以色列的和解,巴勒斯坦成为约旦难以承受的重担
约旦与以色列的和解,同样经历了从“泛阿拉伯主义”到“民族主义”的变迁。现代约旦建立于20世纪20年代的中东动荡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阿拉伯半岛哈希姆(圣裔)侯赛因家族领导的起义军,之所以配合英国军队对抗奥斯曼土耳其军队,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重建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当英国和法国背叛了侯赛因家族,瓜分今天的巴勒斯坦、以色列、黎巴嫩和叙利亚地区后,侯赛因家族也因沙特家族的袭击而失去了在阿拉伯半岛汉志地区的大本营。阿卜杜拉不得不带着残兵败将,向北找英国和法国“要说法”,甚至扬言要与法国人开战夺回叙利亚和黎巴嫩建立自己的国家。但是在英国的劝说下,阿卜杜拉和手下数万人马,留在了外约旦(今天约旦),成立了新的王国。
但是外约旦实在太过贫瘠,以至于阿卜杜拉和绝大多数部下都无法忍受。当时的外约旦首都安曼,仍然是一个只有数百户人口的小村镇,难以承受阿卜杜拉及其家族曾经的“阿拉伯帝国”梦想。当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在1924宣布废除“哈里发”(伊斯兰世界最高权威)制度后,阿卜杜拉一度跃跃欲试想“自我加冕”,但终被当时的阿拉伯精英群体所喝止。当时著名的“泛伊斯兰”主义领导人拉希德·里达就认为,阿卜杜拉能力和德行不足,难以胜任“哈里发”职务。但是阿卜杜拉毫不气馁,一直努力参与和影响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叙利亚事务,力图在英国和法国势力退出后,能够“天下归一”。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和法国撤离近东地区,也只是时间问题。以建立共和制度为理想的黎巴嫩和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反感外约旦的“王国政治”;而约旦河西岸,与犹太复国主义者直接冲突的巴勒斯坦人,成为了外约旦拉拢和影响的主要对象。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外约旦“阿拉伯军团”迅速跨过约旦河,以帮助巴勒斯坦人的名义,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并入了外约旦。
约旦王室的野心,遭到了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反对。阿卜杜拉一世也因为“兼并”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被巴勒斯坦极端分子刺杀于耶路撒冷。随后的数十年里,国王侯赛因执掌国政,力图成为所有巴勒斯坦人的代表。但是巴勒斯坦,却成为了约旦王国国家安全和稳定的“大炸弹”。受到中东战争影响而逃至外约旦的巴勒斯坦人,逐渐成为了约旦人口的绝大多数。巴勒斯坦问题也成为了影响约旦国内政治稳定的重要议题。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侯赛因国王明知参战极有可能战败,仍然在国内民意的压迫下向以色列宣战,最终丢失了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1970年9月,活跃在约旦境内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就因为谋求建立“国中之国”,而遭到了约旦军队的驱逐。巴勒斯坦问题,成为了约旦难以承受的重担。
1987年,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巴勒斯坦民众示威游行,史称第一次“大起义”。“大起义”的爆发,使得约旦认识到,无法再代表所有的巴勒斯坦人。侯赛因国王在1988年7月发布电视讲话,宣布约旦和巴勒斯坦“脱钩”,也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事业的合法代表。侯赛因提出,自己一生中的很长一段时间,都坚持着自己父辈和祖父辈的意愿,即所有的阿拉伯人应当生活在一个国家里。但是侯赛因承认,年轻一代的阿拉伯人,更加希望关注自己的祖国,因此,约旦和巴勒斯坦关系“脱钩”是历史的趋势和必然。
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和解,以色列成为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唯一选择
阿联酋自己的历史同样曲折,民族主义在阿联酋较之其他阿拉伯国家更加重要。作为由七国酋长国组成的国家,阿联酋的诞生就是为了“团结自保”。阿联酋周边强国林立,既有保守的阿拉伯国家沙特,也有传统的阿拉伯强国伊拉克,还有波斯人为主体的强大国家伊朗。阿联酋的国家安全,似乎时刻紧迫且现实。既有被伊朗占领争议岛屿的虎视眈眈,也有来自于“穆斯林兄弟会”等团体的政治威胁,更有内部其他加盟酋长国心怀二心的风险,更有地区国家间“石油大国”“能源大国”同质化的激烈竞争。顺便提一句,阿联酋曾经应该有八个酋长国,那个左右摇摆的酋长国,就是今天的卡塔尔。
因此,阿联酋对于自己的国家安全更加重视,也更加希望摆脱虚幻的“泛阿拉伯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这类政治话语的束缚。从小布什后期开始,美国对于中东的兴趣逐渐降低,美国成为了石油第一大国,不再需要中东的石油。无论是奥巴马还是特朗普,都更加倾向于通过间接的“制裁”手段而不是直接的军事手段,来制衡伊朗。尽管特朗普针对伊朗的“极限施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然难以满足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要求。2003年后,伊拉克国内陷入政治纷争,对于伊朗的制衡不复存在,国内什叶派对于伊朗甚至抱有同情态度。2011年后,埃及经历政权变更,国内经济形势堪忧,无心充当阿拉伯世界领头羊的角色。在此背景下,以色列,成为了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唯一选择。
在今年年初特朗普巴以问题“世纪协定”的发布会上,阿联酋和巴林代表出席,显示出了阿联酋和以色列关系突破似乎近在咫尺。而阿联酋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牺牲的是巴勒斯坦的利益,更意味着对于“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政治理念的抛弃。乔尔·科尔顿在《二十世纪》书中提出“20世纪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民族主义通过作用于各种超民族的意识形态对世界格局进行重构的历史”,民族主义的魔力,在21世纪同样持续和加强。巴勒斯坦人,也许只能依靠自己。
(作者系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叙利亚研究中心研究员)